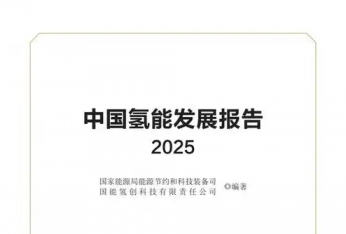人們常說:開門七件事兒,柴米油鹽醬醋茶。這排在最前邊的柴,在很多老北京的記憶中,柴火既是煤火。燒火做飯,冬天取暖,離不開的是–煤。
早年間北京城里人們早晨起來紛紛捅爐子,劈柴,撮煤,籠火燒水做飯。那時的氣溫比如今低的多,特別是一到冬天,家家戶戶屋里必須有煤火爐子取暖。一清早兒,大人孩子屋里屋外的忙活兒。特別是大雜院家家要籠火,院子又窄,有的干脆就挪騰到院外當街上。一到此時,胡同街巷到處是火苗竄起,濃煙滾滾。弄的人人是兩手黢黑,兩眼發紅,流淚直流。那是因為煙熏火燎,嗆的。這一幕,是我自小無數次經歷過的。
就說籠火,是老北京話兒。生火的意思,也有寫成升火的。這活兒雖然看似簡單,可是用具家什不少,煤爐子、拔火罐、爐捅條、爐火筷子……
細細盤算,京城里百姓生火用煤,經歷了支鍋壘灶燒木(劈)柴;燒塊煤;燒煤球;燒蜂窩煤這樣一個流轉順序。
說到京城燒煤,多源于京西北門頭溝一帶。做煤炭生意的煤老板雇用駱駝隊或是牛馬大車,向城墻外的煤場(棧)運煤,并招人制作煤球銷售。說到燒塊煤,有一種產自大同或下花園山溝的煤,老北京稱它“硬煤”。煤價便宜,可是火力不旺,百姓們不待見。大多數人家還是買煤球,買蜂窩煤。
北京城里大量燒蜂窩煤,起源時間大概是七十年代初。而燒煤球,已經是由來已久的。
作家林海音女士小時候曾在城南居住過,對老北京人的生活熟悉,寫出過許許多多京味兒作品,其中有一首市井生活的小詩“撿煤核兒”(發糊的音):
“煤球摻黃土,燒過喚煤核。傾倒入垃圾,棄之同敞屣。窮兒爭取拾,得來如拱璧。……”
這詩中就提到了煤球,而且還將煤球的成分介紹出來了。煤球,就是粉碎的煤末摻著黃土“搖”出來的。而那時,從事這一行當的以河北定興或天津寶坻的人居多,如定興人一開口,就發出“搖(發要)煤球兒地”獨特的鄉音。
我小時候看過“搖煤球”師傅干活。
一般,他們備用兩把切把(剁子)。木把,一把頭上有半米多長厚鐵板,另一把也有但要寬一些。出門干活時,一頭挑著兩個大小孔眼兒(格網)不同的荊條篩子;另一頭挑著鐵鍬和一個瓦盆(類似花盆)。這是吃這碗飯的全部家當。
每日里,他們走街串巷一邊走一邊吆喝:“搖–煤球唻。”當談好價錢后,將煤粉(末)摻上黃土,便開始添水合煤。在平整的地面先撒上細煤末鋪開煤泥,而后就使用切把先橫條再豎條的切出方塊煤餅,待晾干。只見,荊條篩子里均勻的撒上細煤末墊著瓦盆。再將切出寬厚大小的煤塊,鏟進搖煤球的荊條篩子里。剩下的就是掄開膀子,搖啊搖,搖啊搖,搖煤球。然后,把一個個煤球晾曬在太陽地下,自然干燥。這是憑著一把子力氣,吃飯的營生。
我為什么,如此了解這個活計兒呢?我家后院出租的北屋,就居住著一戶張大爺,哥倆兒都是地道定興人,搖煤球的。
買煤的賣煤的,滿面煤黑光剩眼
兒時,我住的地界兒,離家不到二百米,就是個煤鋪——順德館煤鋪。人們都喜歡這么叫它,實際上應該叫前青場煤場。叫順德館,是因為此地在明代建有海波寺,解放后改作海柏胡同16 號院,即順德會館所在地。
此間,有清代浙江秀才朱彝尊居住過,留下了“紫藤、書屋、木涼亭”的傳說佳話。因為這家煤場緊鄰順德館,街坊四鄰也就這樣叫順了嘴兒。
那時買煤,一來是煤場的人每個月走街串巷入戶登記各戶用煤的需求量,送煤上門解決個把月的燒火用煤。二來如果沒有遇到登記或是燒大發了,那就只能自個去煤場買煤。你看吧,賣煤的路上有人推著自家留存的竹板嬰兒車;有的拉著自制的軸承車,一塊木板下四個軸承,再放上一個破筐;還有人騎著自行車,后車架子綁扎個木箱子或紙箱子;沒有這些的干脆就是一條扁擔兩只水筲(老話兒鐵水桶),自己往回挑,那才叫五花八門,各顯神通呢。
由于這家煤鋪是開在胡同口的西邊,街坊四鄰買煤時,有人會開上一句玩笑話兒:“大哥。我挑起這擔子,走西口去了。這家里屋外的托付給您,麻煩多給照應著吧。”
到煤場再看,油氈棚高高大大有頂棚,但四面是漏風的。這簡易的棚庫里,堆積著比一房還高的蜂窩煤。緊鄰的就是壓制蜂窩煤和煤球的機器,里面干活兒的師傅口罩帽子衣裳鞋子被涂染著黑煤粉,只剩下眼球還算是白的。
煤場北邊是傳達室,南邊臨街的房子玻璃窗戶留了一個活動窗口。窗下一張方木桌,一把算盤,紙筆和一摞摞找零的鋼镚兒。墻外則掛著一個銷售價目的牌子,一清二楚寫上蜂窩煤、煤球、煤塊、引炭、劈柴和爐瓦、膛爐灰的價格。
買煤在窗口交了錢,收費的師傅就將捆綁成一對的竹片牌兒,一個交給你,另一個留存記賬。竹片牌子上用紅漆寫著煤的數量,其中一個打著小孔系有一條小線。隨后你推著或拉著車來到棚庫前,那里的師傅收取了牌子后就趕忙給你裝煤。他一邊“倒煤”,一邊大聲一五一十叨嘮著,好讓你聽清楚裝煤數量。
前青場煤場地面低于馬路,裝好了煤后師傅會主動幫助推車或對挑擔的給“抄上一把”。遇到不小心摔碎了蜂窩煤,師傅們會將碎煤扔回煤堆再幫助換回成塊的。那時還經常在胡同街巷里遇到送煤的師傅,費力的蹬著裝滿煤的三輪車,趕上了下雨苫布遮不住一車煤,他們會毫不猶豫的脫掉身上的雨衣,蓋在蜂窩煤上。那時的一句贊頌話,是“弄的一人黑,換回千家暖”。
煤火雖有溫暖,但文明行走到今天,家家改用了天然氣、煤氣,燒水做飯洗澡也改用了電磁爐、電炊具、電或是燃氣的熱水器,即快捷又干凈,這是社會文明的象征。聽說今年全北京還會加快煤改電,一下又將減少45萬噸燃煤。
一句話,煤火不見了,北京城里的人享清福過清潔日子,是社會進步了。 來源:北京晚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