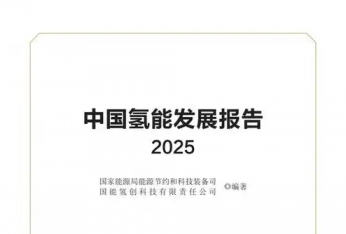西寧路社區不少居民在家中要裹著被子。 社區供圖
在石景山與門頭溝兩區交界的西六環高架橋旁,靜靜地矗立著一片紅磚樓。這些樓建于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隸屬于門頭溝西寧路社區。住在這里的居民大多是鐵路職工,來自天南海北。
西寧路紅磚樓是企業自供暖。也許是因為設備老化,也許為了節約用煤,這里每天分四個時段供暖,到了晚上11點之后,暖氣基本就沒有多少溫度了。因此在漫長的冬天里,西寧路紅磚樓里的居民們最希望看到兩種風景:一種是天空中升起暖洋洋的太陽,一種是鍋爐房的煙囪冒出熱騰騰的白煙。
冬天在家不敢脫衣服
上周六下午,西寧路1號樓六層一個兩居室內,張先生裹著被子坐在床上,不停地咳嗽。此時,室內溫度計顯示有16℃。“平時住在項目工地,回來兩天就感冒了。”
張先生說,當天天氣預報最高氣溫是6℃。根據北京市供暖規定,氣溫在零下7℃以上時,老舊小區的室內溫度應該達到18℃。“我們這里經常達不到標準。”
據張先生介紹,西寧路的居民大多是一家鐵路企業的職工,冬天是單位自供暖。“每天一早一晚,上午下午分四個時段供暖,夜里11點之后鍋爐封火,暖氣慢慢就涼了。”
張先生說,小區里住著很多退休職工,年紀都不小了。“人上了年紀就怕冷,冬天屋里只有十幾度,進門都不敢脫衣服。中午外面陽光好的時候,屋里感覺還沒有外面舒服。”
晚上蓋八斤重厚棉被
每年10月,住在西寧路3號樓的劉女士就會把自己八斤重的厚棉被找出來晾曬。“過冬就靠它了。”劉女士說,現在人們都喜歡柔軟蓬松的棉被,可她還真離不開這條絮了八斤棉花的大厚被。
劉女士說,小區每天分時段供暖,她沒有掐算過準確供暖時間,平時主要看窗外不遠處的鍋爐房來判斷是否開始供暖了。“只要開爐供暖了,鍋爐的煙囪就會冒出白煙。”
這天下午兩點多,冬日的暖陽照進房間,劉女士看看窗外,鍋爐房的煙囪飄著稀疏的煙,伸手摸了摸暖氣,不覺得熱,也不覺得冰手。“天氣好的時候,供暖時間也會減少。”劉女士說,入冬以來還不是特別冷,白天暖氣不熱,也基本上能保持15℃至16℃,可到了夜里,暖氣基本沒有了溫度,要沒有一條厚棉被,漫漫長夜還真是難熬呢。
除夕夜停暖凍跑親友
劉女士回憶,上世紀90年代初,小區剛建好時,冬天供暖還真是沒的說。“那時比現在冷,可屋里的暖氣足,如果不開窗就會覺得熱。”劉女士說,大約十年前,小區開始分時供暖,而且到了晚上還經常停水。
小區房管辦向居民們解釋,由于管道老化,無法保證全天恒溫供暖。在供暖季到來前,劉女士和鄰居們也經常會看到,胡同里挖出深溝,已經銹蝕漏水的管道被丟棄在路旁。“基本是哪兒壞了修哪兒,就是一直沒有徹底解決。”
劉女士還記得兩三年前的一個除夕夜,幾位親友留在家里打牌。夜里十一點多的時候,暖氣已經有些涼了,房間里的溫度下降到10℃左右。她的嫂子冬天怕冷,在涼屋子里待久了身上就會過敏,長出紅包。眼看就到十二點了,嫂子的身上長出大片的紅包,渾身刺癢難擋。劉女士也不敢留她一起守歲了,趕緊打車給送回了家。
無 奈
空調成暖氣必備“伴侶”
每年冬天分時供暖,像劉女士這樣的老住戶已經基本習慣了。而一些新住戶就有些不適應了。
李阿姨和老伴兒因為住房拆遷改造,開始在西寧路租房居住。今年是他們在這里度過的第二個冬天。“我們這房間里的暖氣一直就是14℃至15℃,必須長期開著空調。”李阿姨說,因為吹空調干燥,屋里還要擺上兩盆水增加濕度。
白天暖氣就不熱,最難熬的還是夜里。“有幾次夜里真是被凍醒了,一摸暖氣都是涼的。”李阿姨說,剛搬來那一年,因為冬天晚上沒有暖氣,她起來上衛生間,穿的衣服少了,結果還被凍感冒了,在醫院輸了幾天液。
李阿姨家的鄰居也是一個租戶,兩個年輕人帶著一個孩子。小孩兒白天上幼兒園還好說,晚上回來家里只有十幾度,孩子冷得直流鼻涕。“他們又沒有空調,我就經常讓孩子到我這來玩兒,到睡覺的時候再抱回去。”
爭 議
分時供暖居民反應不一
對于分時供暖,西寧路的居民們的態度不盡相同。在這里租住了幾年的羅先生表示,每年冬天都要按面積交供暖費,供暖企業應該保證供暖達標,不能分時段送暖。
而退休職工王先生表示,雖然分時段供暖不能保證全天溫度都達標,但收取的供暖費也要低于其他小區。“這里一個供暖季只需要幾百塊就夠了。”
王先生說,分時段供暖也符合節約理念。“天氣不冷就少燒點煤,晚上睡覺時,就把爐火封起來,以前我們自家燒爐子取暖也是這樣嘛。”
改 造
明年改造鍋爐保恒溫
近日,記者來到為西寧路紅磚樓供暖的鍋爐房外探訪,對居民反映的分時供暖情況,一位工人說:“一天就給四回熱氣兒,廠里就是這么規定的。”西寧路社區居委會工作人員表示,由于紅磚樓屬于企業自供暖,因此主要還需企業自己解決。
據西寧路鐵路職工宿舍區房管辦工作人員介紹,分時供暖主要是因為鍋爐老化等原因,企業才采取的無奈之舉。據該工作人員透露,預計明年,企業將對鍋爐進行改造更新,那時供暖水平就會上一個層次,最起碼達標沒有問題。目前,如果住戶家中不熱,可給房管辦打電話報修。
本版撰文 晨報記者 王歧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