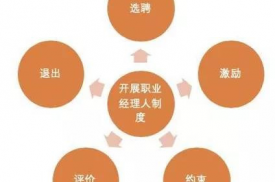只有對未來看得更長遠,才會對當下各種挑戰、風險和波動更加淡定和有信心。
編輯|馬吉英
頭圖來源|中企圖庫
12月10日~11日,由《中國企業家》雜志社主辦的“第二十屆中國企業領袖年會暨第二十二屆中國企業未來之星年會”隆重舉行。在“尖峰論壇:投資人如何穿越大周期”環節,如是金融研究院院長、首席經濟學家管清友作為主理人,與明勢資本創始合伙人黃明明、天圖投資管理合伙人潘攀、洪泰基金創始合伙人、董事長盛希泰、梅花創投創始合伙人吳世春作了交流。
其核心觀點如下:
1.作為一個科技領域的風險投資人,要想方設法把眼光拉得更長,因為只有對未來看得更遠更長,你才對當下的各種挑戰、風險和波動變得更加淡定和有信心。
2.周期不可逆,學會接受,學著做出應對策略,學會適應它。
3.一個市場環境偏嚴苛的行情,反而是投資機構的一個機會,這個時候很多好項目不需要搶,可以從容地跟他們談判,以非常好的一個估值談下來。
4.技術不能閉門造車,不是在高大上的辦公室、實驗室里,一定要和中國廣袤縱深、巨大的產業鏈進行深度結合才能爆發出巨大的價值。
5.宏觀環境變化下,本質上是對整個企業估值體系重構了一遍,包括科技股、醫療股、消費股。
6.你能夠搞定核心客戶,就是市場上最能夠生存、最能夠適應周期的公司。
7.作為早期投資人,如何能夠不斷地跟上每一代人,跟他們的觀念一致,成為不落伍不掉隊的人,站在主流舞臺,這個很重要。
以下為對話整理(有刪減):

管清友:請問各位在這幾年特別是2022年,自己投項目、投賽道的感受如何?
黃明明:我們知道過去幾十年中國是全球經濟的火頭車和發動機,也是最有活力和最有生命力的創投企業的土壤,包括風險投資也在這里非常活躍。當下,大家非常關心的就是目前國際國內大的環境,我們怎么看中國的創投。

我們明勢資本從成立之初就聚焦在科技創新這個賽道。我覺得作為一個科技領域的風險投資人,我們要干的事情是想方設法,把眼光拉得更長,因為只有你對未來看得更遠更長,你才對當下的各種挑戰、風險和波動更加淡定和有信心。
我們看到未來5~10年,一個巨大的確定性是通過算力的持續提升,以及人工智能技術對算法的持續優化,電腦處理能力大概率在未來10年會超越人腦的處理能力,大家想想這是一個多么激動人心的未來。
自動駕駛我們都知道,可能是人工智能最先落地的場景,后面我們看見埃隆·馬斯克也在特斯拉AI Day發布了有學習能力的機器人。也就是說,我們未來面臨的是一個算力算法疊加在一起是今天的一千倍、甚至一萬倍的新型智能,而且電腦具有它的學習能力,這樣的未來是令人無比興奮和激動的。
現在,好像確實有不少同行選擇放慢速度或者躺平,我們的投資速度跟去年、前年相比不光沒有降低,反而還在提速。投資人要訓練自己有超越常人、看得更遠的視角,當你把視角拉到5年后或10年后,你會看到非常多激動人心的機會和非常激動人心的未來。
潘攀:我講一下我今年的一些感受,因為我們年終也在做總結,大家都在聊這個事。
第一,接受周期這個事。我覺得周期是一個不可逆的事情,對所有人來說首先是心理上的接受。
第二,根據不同的周期做出不同的應對策略,我覺得沒有一個策略是永遠對的,對投資機構也是如此。
第三,我們自己看到一些有意思的情況。像那種百年或者幾百年歷史的大的跨國消費公司,它們在中國在加大投入,甚至把中國市場列為全球最重要市場。
我們有個LP是雀巢,在深度溝通中發現整個中國市場在它全球份額中變得越來越重要,且級別也越來越高。這些公司都是幾百年歷史,經歷了周期,知道什么樣的市場值得長期投入,這對我們來說是非常正向的指標。
我們也堅信中國的消費企業經過10年、20年增長,也會出現中國的雀巢、中國的歐萊雅、中國的星巴克。
吳世春:我們基金一直是中國最樂觀的早期基金,從成立開始我們每年投的數量,投的領域,都是比較廣比較多。我們今年到現在為止也投了80多個項目。我們既投消費也投產業升級,也投科技升級。

過去三年,在我們定義的新半軍數智航里面做了大量投資,像新能源、半導體、軍民兩用、大數據、智能制造、商業航天。最近我們還對一些上游科技做一些投資,和一些開采技術的公司。
我覺得這樣一個市場環境偏嚴苛的行情,反而是投資機構的一個機會,這時候很多好項目實際上不需要搶,你可以從容地跟他們談判,去以非常好的一個估值談下來。
宏觀你是改變不了的,你只能去適應它,所以我為什么寫了《自適力》,適應未來、適應宏觀、適應高維,你才能夠比別的同行更有生存能力。所以我們把自己定義為一個兩有三懂的機構,叫有業績、有生態,懂產業、懂政府、懂技術。
盛希泰:我跟明明和世春比,他們屬于洋派,我屬于土派。我做投行做了20年,做A股更熟悉一點,原來投行深耕的也是二三線城市,我覺得最近這幾年找到一種特別熟悉的味道。
我一個特別深刻的體會是什么呢?行政周期大過市場周期,全世界只有中國是這樣。最近三年的變化就是行政周期的調整,市場周期的調整占的比重沒那么大。
另外有個現象很有意思。2017、2018、2019、2020、2021,這幾年我們單個IPO募資金額是美股的1/2都不到,而今年反過來了,今年A股單個IPO金額是2.1億美元,正好反過來是美股的兩倍。這個變化也很有意思,整個來講我覺得特別特別振奮。
我仍然對中國投資非常有信心在哪里呢?我就說一個數據。目前為止A股有將近1000家在排隊IPO,有3200多家企業在排隊進入輔導期,4000家企業就是希望、未來。過去十多年,上市公司大部分是互聯網公司占主導,而廣大幾千萬家企業除了上市公司以外,他們大部分沒有真正成功。我到二三線城市收獲很多感動,這些企業家基本上年齡都比較大,創業時間很長,掙一分錢都投入到擴大再生產,我覺得這是希望、未來。
你在北上深跟互聯網企業家一聊,跟房地產商一聊,得到的結論和你的心情,和你到三線城市跟這些科技實業企業的人一聊的心情是完全不一樣。我覺得扎根三線城市,農村包圍城市,收獲特別特別不一樣。
從投資來講發現一個什么現象呢?原來我們講一定要做行業研究,挖掘投資標的。現在發現你只做行業研究可能會摟空,為什么?因為過去十年很多實業企業沒做過PR,也沒報道過,名不見經傳,而它在行業里面也很有代表性。
我發現什么呢?你扎根三線城市去深度挖掘,去做地毯式搜索轟炸,同時再跟行業研究結合,有可能得到一個比投資標的更完整的全貌。
原來你在北上深很容易打到獵物,但你如果現在仍然這樣是摟空槍。當然你做行業研究深扎也是可以摟到好企業,但是我覺得摟得不完整。投資人為什么有的時候也會踩坑呢?因為所謂的DD不是萬能的。你如果在企業里待的時間很長,或者你去駐扎時間比較長,這個企業有些東西很難通過包裝手段把你蒙蔽過去。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我覺得也有利于更高地提高投資質量。

還有一點是什么呢?政府特別歡迎投資人幫他做一些產業顧問,幫他篩選一些招商引資的項目。
時代真的變了,整個戰場轉移到了二三線城市,而國家堅決認為這些企業能夠解決卡脖子,是支撐中國的希望、未來。過去十多年出現過幾家十萬億、幾十萬億的公司,那對國家來講有另外一個選擇。如果說政府通過推動產生十萬家1個億的公司,一萬家十個億的公司,一千家100億的公司,加起來體量差不多,政府選哪一個呢?毫無疑問選第二個,第二個一定是代表希望未來,一定是底座更扎實,對政府來講各方面都比較好調控。
時代真的變了,國家級專精特新企業超過80%都在三線城市,不在一線城市。這是我的觀察,因為今年我基本上大部分時間沒在北京,我在北京可能待了兩個月時間,我跑了十幾個省,跑了幾十個城市,現場看了幾百個企業,我得出這個結論。我覺得這些企業需要被關照,需要更多資本的關照,政府也很需要,也很有饑渴感。

技術不能是閉門造車
管清友:我想請黃總跟我們分享一下,目前我們說能穿越周期的這些要素哪些變了,哪些沒變?您是不是感覺到,我們可能要超前布局,用和過去不一樣的方式去投資,不是只在北上廣深,可能要深入到三四線城市去?
黃明明:明勢投的很多項目其實是在二三線城市,甚至更偏遠的地方,我們的投資經理經常為了看一個項目要飛機、高鐵,還要換大巴,才能到那個企業的所在地。
這里面其實原因是什么呢?我覺得是背后的技術,不管你是做什么樣的技術,最好的技術一定要和產業進行密切結合才能爆發出巨大的價值。
我們一直講技術不能是閉門造車,不是在高大上的辦公室里、實驗室里就行的,一定是要和中國廣袤縱深、巨大的產業鏈進行深度的結合才能爆發出巨大的價值。
所以我們投的很多企業在某些領域技術有非常強的前沿性,同時又和產業結合得非常深。
但我想強調一個觀點,就是過去幾年大家都轉到科技創新的賽道,包括投資卡脖子的領域,但是我們明勢不太喜歡純粹做國產替代的項目。
比如,我做到國外同類競品的六七十分,但是我的價格可能是它的50%甚至更低,這樣的企業我認為在今天的國際國內大環境下,尤其地緣政治角力的情況下,肯定是有它的市場價值,甚至在短期之內它的估值也會被很多投資機構所追捧。
但是我們更喜歡我剛才講的,企業家從一開始的目標就是五年后、十年后,希望做成世界級的科技企業。兩個企業起步的時候相差不遠,但企業家從一開始的目標、格局、眼光不一樣,就決定了這個企業的未來發展,可能是一個天上一個地下。
我們不管地方在哪,只要這個企業家和團隊有這樣的潛力和雄心壯志,那我們就去堅定地支持他。
管清友:說的非常好。我覺得您對國產替代這個提法,特別值得我們一些被投項目做參考,我覺得業界和政府都要聽到這個聲音。
另外,從投資機構這個視角來講,我最近幾年也確實發現很多都是在往三線四線城市跑,很多投資人說我們從原來所謂西服、皮鞋,開始變成背著一個小包到田邊地頭,跟人民群眾打成一片。
我們今天討論的主題是穿越大周期,這個周期已經超越所謂經濟周期,是這個世界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一個周期。
我們從微觀轉到宏觀作一點探討,我想請潘總接著討論這個問題,從您這個角度看,哪些大的因素真正會對你們投資的賽道、投資的項目、投資的方式產生重大影響?你們覺得哪些因素最重要?時間節奏上你們怎么把握?
潘攀:我覺得周期這個事不可避免,我相信2019年的時候,在座的沒有任何一位能預測到疫情這個事,其實核心我覺得是應對。
在這種宏觀環境變化下,其實本質上是對整個企業估值體系重構了一遍,今天我們看包括科技股、醫療股、消費股,估值變化了,二級市場變化了,其實一級市場肯定會有相應的變化,我覺得這是對大家比較大的沖擊。
我相信今天所有的頭部機構也都在后悔,為什么沒有在市場好的時候,把最好的公司至少賣出一部分。所以我覺得估值體系肯定是對未來有深刻影響。將來比如說依然出現一些巨頭或者某個行業的巨頭,它也不一定會給那么高的估值。當然我覺得市場也可能有周期恢復,但目前可見的3~5年之內是一個相對比較明顯的市場需要恢復的周期。
結合宏觀來看,到底什么企業長期能穿越周期?我們今天看消費本質還是在看創新。
我們重新去看那些穿越周期企業的成長史,發現它本質上還是創新的事。比如說你去看雀巢、歐萊雅的年報里面,有多少全球最頂尖的科學家在里面。你說它是消費企業?是,很明顯的消費企業。但你去看它每年在科技上面的投入和人員的投入有多大?
我們今天看宏觀環境的變化,其實本質上還是取決于企業怎么應對,最好的應對還是創新,創新對消費企業而言逃不過科技創新、材料創新。


把決策的顆粒度不斷切細
管清友:這個話題我們引到所謂的企業如何去適應周期的問題,有的人是高瞻遠矚,有先見之明,能踏準節奏。但是常識告訴我們,這是極少數,而且需要極好的運氣,大部分人我覺得還是要在這個周期當中蹚過去,這其實是非常復雜的一個過程。
吳總既然寫過《自適力》這本書,在實踐當中也在投很多企業,您能不能給我們分享分享規律,也給大家一些建議,如何去適應周期?
吳世春:對,我們以前覺得這種變化沒那么快的時候,大家可以按年度,甚至按幾年去定一個計劃、做一個預測,但現在我覺得這種顆粒度越來越細。我知道像字節跳動已經按倆月做,不是按季度,按倆月進行復盤。所以應對環境的變化,如果你的時間周期顆粒度越小的話,你越容易靈活去調整。
現在不管做投資也好,一個企業的管理也好,都不要去做很長時間的預測、很長時間的計劃,預測都是啪啪打臉的。
我們認為快速地去適應,快速地去把一些新常態當作自己的基礎變量或者既定假設,然后放到自己的每一個決策里面來。我們希望是每個月都在復盤自己的投入ROI產出,最后該裁人裁人,該控制開支控制開支,這樣你到現在可能會活得比同行好很多。
所以我們相信自適力就是你的決策把顆粒度不斷切細,變成我下周該怎么辦,我明天該怎么辦,這個月的月會我要不要決定下個月裁員,要不要去應對。
所以我們不投那種需要埋頭狂奔幾年去完成一個長周期研發的企業,這種接不到客戶。我覺得現在訂單能力就是高科技,你能夠搞定核心客戶就是這市場上最能夠生存、最能夠適應周期的公司。
管清友:我最近體會到從創業和做企業這個角度來講,它是個非標準化的東西,我們可以總結很多所謂的共識或者同類項,但是很多時候確實取決于企業家,或者機構主要負責人、創始人的審時度勢適應能力。

最后我想結合咱們討論的這個議題,給各位提同樣一個問題,現在最大的一個影響周期性的因素是什么?
黃明明:我還是講我們自己堅持的觀點。就我們認為唯一能穿越周期的一定是科技創新類的企業,一定是科技創新來推動人類社會穿越迷局,穿越周期,走向光明的未來。
在不遠的未來,我們人類做出來的機器,它的處理能力會第一次超越我們人腦的處理能力,十年之后這個世界上的能源結構一定跟今天我們的能源結構有個翻天覆地的變化,百分之八九十的車,包括很多其他的動力單元,一定是由傳統的化石能源到新興能源和可再生性能源,這里面帶來的都是無比巨大的機會。
誰能夠突破這些技術,持續創新和挑戰,然后在產業里面找到自己的結合點,我們認為這個是最大的突破點,當然也是最大的挑戰點。任何能夠挑戰和突破這些巨大瓶頸或者巨大困難的企業,一定是在未來會產生最大價值的企業。
潘攀:我們自己這么總結的。第一,我們覺得企業長期的核心競爭力和穿越周期不變的東西本質上是創新。對我們看消費或者看2C而言,創新我覺得有三個方面,一是科技創新帶來的巨大供應鏈的升級;二是材料上的創新;三是組織效率的創新,就是通過新的商業模式、數字化的經營方式,本質上是機器取代人工,用算力來更精確地把所有組織更有效地分配在各個環節上面,所以對消費企業而言我覺得穿越周期的本質還是創新。
吳世春:技術周期非常容易變得衰落,我覺得技術周期是弱于經濟周期的影響,經濟周期又弱于政治周期的影響,政治周期弱于人口和觀念周期的影響、意識形態的影響。
我們最害怕的還是這種類似于觀念周期,就是每一代人都有一代人的觀念,你的投資能力,你的認知如果跟不上新的時代觀念,有可能你就是out的。像當時納斯達克科技泡沫,很多人嘲笑巴菲特,結果發現巴菲特投的那些東西,反而能穿越這個周期。
作為一個早期投資人,如何能夠不斷地跟上每一代人,站在主流舞臺,跟他們的觀念能夠一致,能夠成為不落伍不掉隊的人,這個很重要。
管清友:這個確實是非常不容易的,其實大家都看到了穿越周期的不同側面,話題簡單,答案其實非常復雜。
盛總,您覺得最大的制約穿越周期的因素是什么?您有哪些繼續深耕中國經濟的建議?
盛希泰:影響一個企業發展的4個要素,第一,國際大環境變化,我們必須要創新。第二,國家的需要,社會的需要。第三,所有資源的集中配置和支持。第四,最大的市場。我想這4個因素完美結合意味著中國未來十年代表著希望、未來。
管清友:謝謝盛總,觀點非常明確,其實我們可以這樣總結,就是圍繞國家發展的方向。正好我們也是在黨的二十大重要會議召開以后,探討的這些問題,中國經濟潛力無限,可以說我們都是立足中國面向世界,匯聚全球力量,匯聚全球資源。我相信企業之間會大浪淘沙,經濟周期會永遠存在,但是我們穿越周期的智慧永恒。